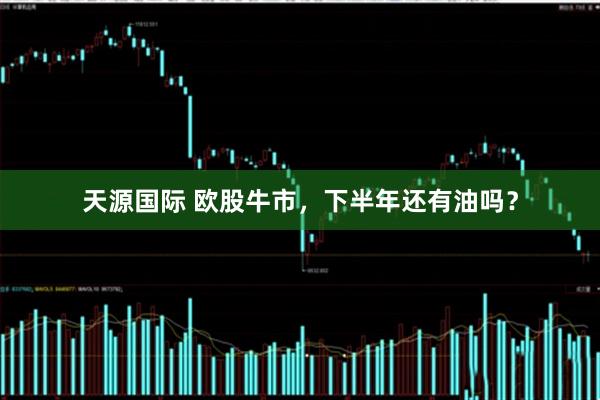那年北京刚入春掌上策略,街头的雪刚化,菜市场还是一片泥泞。
一位穿着灰布棉衣、说话温声细语的妇女,在摊上摆了几包散装香烟。
她不吆喝,不抬价,只是静静坐着,偶尔把摊上的烟盒摆正,再轻轻咳一声。
没人知道,她曾住在紫禁城的高墙深宫里,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妹妹,是地地道道的格格。
她叫·韫颖。

而就在这个摊子前,,当时的中央文史馆馆长,站住了脚。
他看了她一眼,再看一眼,忽然说:“你不是普通商贩吧。”
那一次偶遇,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,也让毛主席看完她的自述信后,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:
“她是个有志气的人,安排工作。”
可一个皇室出身的格格,怎么就走到了北京街头卖烟的地步?

1913年,韫颖出生在北京城的皇宫里,那时的大清虽然已经灭亡,但袁世凯答应清室提出的“优待条件”,紫禁城里依旧灯火辉煌。
她是溥仪同父同母的妹妹,排行第三,大家都叫她“三格格”。
她小小年纪,生活已被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每天早上有人伺候起床,奶妈端水,宫女梳头。学堂里有专门的老师教她古文、诗词、礼仪,还要学怎么端茶、走路,坐姿也要“像个格格”。
她从没见过银钱长啥样,更没碰过油烟和扫帚,那个时候,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会这样过下去。
可她不知道,宫外的世界,早已换了天。

1924年,冯玉祥一声令下,清室被逐出紫禁城。
那年她十一岁掌上策略,跟着哥哥溥仪一道收拾细软,被士兵押着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宫殿。
紫禁城的大门在她身后关上,咔哒一声,像是命运上了锁。
出了皇宫之后,他们一度在天津落脚,后来又辗转到了东北。
成年后的韫颖,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,婚礼简单,却被溥仪称作“皇室最后的体面”。
新婚不到一个月,丈夫被送往日本学习骑兵战术,韫颖也一同前往。她以为是出国深造,结果到了日本才明白,她是去当花瓶的。
她被安上“妇女会会长”的头衔,跟日本贵妇打交道、出席活动,但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。丈夫每天训练摔得遍体鳞伤,她则像关在笼里的金丝雀。
她给溥仪写信说:“我想回家,我不是他们的玩偶。”
后来,随着伪满洲国成立,她才以“探亲”名义回国,与丈夫团聚。但那不过是从一个笼子,换到另一个笼子。
在伪满洲国的几年,她穿着锦缎,却再没有过自由。


1945年,日本战败投降,伪满洲国土崩瓦解。
溥仪和润麒都被苏联红军带走,作为战犯押往西伯利亚,而韫颖,带着三个孩子,留在了满目疮痍的东北。
她没有钱,没有人脉,更不会养家,她卖掉仅剩的珠宝首饰,开始在人群中摆摊。
有人认出她的身份,骂她“卖国贼的老婆”“清朝的走狗”,她只能收摊躲避,再换个地方重来。
但三个孩子还在长大,病了得吃药,饿了得吃饭。
她没别的本事,只好打碎骨头咽下去,学着怎么当一个普通女人:洗衣、缝补、讨价还价。
最后,她学会了卖烟。
最开始生意不好,她一狠心,把整包烟拆开,一根根卖。
有人看她不像个小贩,她说:“为了孩子,我什么都能做。”
1955年春天的某个清晨,章士钊在东城菜市场走了一圈,忽然在烟摊前停住了脚。他看了几眼那个坐着的中年女人,开口问:
“你是爱新觉罗·韫颖?”
韫颖抬起头,眼里满是惊讶。

那天,他们在摊前聊了很久,章士钊回去之后,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,随信还附上了韫颖写的自述和一本记录旧宫生活的《满宫残照记》。
主席读完后,只说了一句话:“她是个有志气的人。”
很快,周总理亲自安排,给她在街道办找了一份文员的工作。
韫颖站在那张聘书前,半天没说话。她后来回忆:“那天我才知道,什么叫做温暖。”

在街道办,韫颖一干就是几十年。
她帮人调解纠纷,宣讲新婚姻法,谁家有困难她都第一个赶到,没人再叫她格格,大家都喊她“韫姐”。
她从不炫耀身份,直到丈夫润麒从战犯监狱被特赦,两人团聚,她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,住在老北京的一条胡同里。
有一年春节,周总理和邓颖超请他们夫妻来中南海吃饭。周总理笑着说:“你现在是我们的同事。”
饭桌上,韫颖低头笑了没有珠钗,没有宫装,却比当年更动人了。
她晚年常说:“要不是国家帮我,我可能早死在街头,是共产党让我重新做人。”

1992年,她安然离世,丈夫润麒把她的遗像摆在家里,一直没动过。
韫颖从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格格,变成了街头卖烟的小贩,再变成了人民的办事员。
她这一生,是从历史的高墙里走出来,真正走进了人民里。
这,或许比当一辈子的格格更难,也更值得尊敬。
广盛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